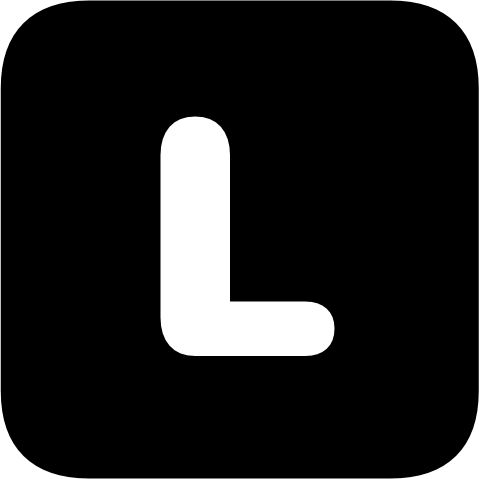若无意指认那在伤感中徘徊、欲望中沉浮的生命就是我们本来的生命,那么,总还有别样干净明亮的生命,等着人去认领。 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一个地方有传说,就是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是阿勒泰的一次绝唱。 风里来...
我们实在没法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要求。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五十只?一百只?”
“七只。”
“啊—”太不可思议了,“七只鸡少了三只,你公公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 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 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时,它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地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唯有墙根蒙着的一层冰霜)。它只好攀着栅栏,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嚼食滚落进笼子里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
每天,我一个人做好饭,汤汤水水、盆盆罐罐地打一大包给村头店里那些干着活、等着饭的人送去,一个人穿过安静明亮的喀吾图小村。白天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一只鹤走来走去,时不时会迎面碰到。我送了饭再一个人走回家,经过一座又一座安静的院落、房屋。我也想一家一家推门进去看看有没有人。如果有人,我也会靠在人家门口看半天的,不管他在干啥。真寂寞呀。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小姑娘的妈妈始终凑不出来。也可能手头不差这点钱,想着反正是自己的东西,迟一天早一天都一样的,别人又拿不走,所以也不着急吧。但小姑娘急,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巴巴地捏着新衣服袖子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就这样,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家里挂着!最后,还是我们最先受不了了…终于有一天,当这个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那个乐呀!紧紧攥着衣服,满面喜色,欢喜得都不敢相信了,都不敢轻易离开了。她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看我们都不理睬她了,这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隔开, 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吃饭时就全部挤到外间,紧紧围绕着缝纫机上的一盘菜。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每次都成功地令他们大吃一惊,迅速转移注意力。
在那时,当地人都还没见过真正的金鱼,只见过画片和电视上的。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梦一样的尤物一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妙曼地晃动、闪烁,透明的尾翼和双鳍像是透明的几抹色彩,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而窗外风沙正厉,黄浪滚滚,天地间满是强硬和烦躁…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回头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微妙地软下去许多。
就这样,钱贷到手了,虽然不过三千块钱,但是不好意思的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还。
据我妈的说法是:那个银行的行长调走了,实在是不知道该还给谁…也从来没人找上门来提这事。况且后来我们又搬了好几次家。
二〇〇九年补:二〇〇六年夏天,那笔钱到底还是还掉了。因为那个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到夏牧场走亲戚,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不小心竟撞进了我们家……
总的来说呢,河边还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河边深密的草丛时刻提醒你:“这是在外面。”外面多好啊,在外面吃一颗糖,都会吃出比平时更充分的香甜。剥下来的糖纸也会觉得分外地美丽—真的,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糖纸的,好像这会儿才格外有心情去发现设计这糖纸的人有着多么精致美好的想法。把这鲜艳的糖纸展开,抚得平平的,让它没有一个褶子,再把它和整个世界并排着放在一起。于是, 就会看到两个世界。
就这样,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光里,身体自由了,想法也就自由了。自由一旦漫开,就无边无际,收不回来了。常常是想到了最后, 已经分不清快乐和悲伤。只是自由。只是自由。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死去的,到那时,我会在瞬间失去一切,只但愿到了那时,当一切在瞬间瓦解、烟消云散后,剩下的便全是这种自由了•只是到了那时,我凭借这种自由而进入的地方,是不是仍是此时河边的时光呢?
我们这里的小孩都很厉害的,他们每天赚的钱比我们开一天商店赚的还多。我们开商店赚出来的钱全让他们给赚走了。鱼五毛钱一条;湿的黑木耳十块钱一公斤,干的六十块钱一公斤;一公斤草蘑菇换一个苹果,一公斤树蘑菇两块钱;凤尾蘑菇、羊肚子蘑菇,统统八块钱一公斤•甚至树上长的耳朵形的树瘤也一批一批送过来,总觉得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被汉人派上用场似的。不管和他说多少遍“我们不要这个”也没有用。而自家制作的酸奶、干奶酪、甜奶疙瘩、黄油⋯•• 更是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弄走我们家货架上一棵又一棵大白菜、棒棒糖和汽水。还有的孩子摘到了一把野草莓,也想便宜点卖给我们, 小小年纪就这么财迷心窍!于是我们把他的草莓骗过来吃得干干净净,并且什么也不给。他便哭着回去了,从此再也不往我们家送草莓了。
她一个人裸着身子在山野里走,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只有她一个人。她又走进一处森林,很久以后出来,双手空空。她有些着急了。但是望一眼对面山上另一片更深密的林子,心里又盛得满当当的,那里一定会有木耳,一定会有虫草的。还有希望。她一个人⋯..
当她一个人走在空空的路上,空空的草地里,空空的山谷,走啊走啊的时候,她心里会不停地想到什么呢?那时她也如同空了一般。又由于永远也不会有人看到她这副赤裸样子,她也不会为“有可能会被人看见”而滋生额外的羞耻之心。她脚步自由,神情自由。自由就是自然吧?而她又多么孤独。自由就是孤独吧?而她对这孤独无所谓,自由就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吧?
后来我们很快把这件事忘记了。生意不好,我们只好天天跑出去玩,爬山、采木耳、采蘑菇、钓鱼,日子永远不会太无聊。
直到有一天,一个风尘仆仆的牧人在我家帐篷前下马,捎来一块黄油,一包红绸子包裹的干奶酪,还有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纸片儿,上面一笔一画地,紧紧地挤着三个汉字:哈甫娜。
我立刻想起了那个草地上的美好下午。
我们现在很快乐,可哈甫娜在深山里,左右无邻,终日和牛羊为伴,一定非常孤独吧?
我趿着拖鞋走在晴朗天气里的草原上,脚趾头从破了的袜子里顶出来,不时碰着青草。走了很远,又踢掉拖鞋走到河边的沙滩上,小心地避开一丛丛生有细刺的植物。远方真美!那些连绵起伏的森林, 青葱草坡,闪耀着无数条纤细溪流的峡谷⋯而我不能去向那里。我赤脚站在河岸边的一处高地上眺望,要是有一双永远穿不破的鞋子该多好!那时任何一处我想去的地方都会随着我的到来而平坦舒适吧?…总是想去那么多的地方,但却总是有那么多的原因,让人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