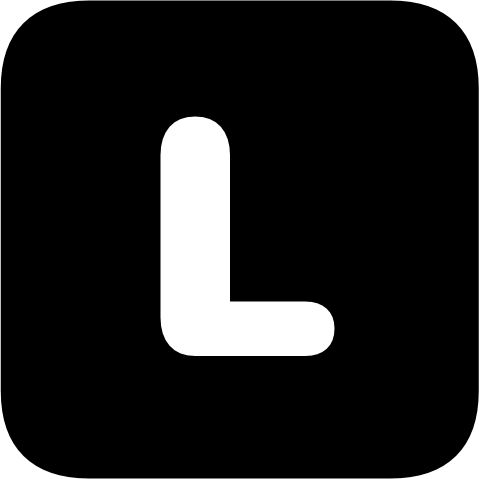火遍微博、微信的《小崔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首部回忆录 比尔·盖茨2017年夏季书单推荐图书 美国《纽约时报》《新闻日报》《时尚先生》及“国家公共电台”年度好书 2017年瑟伯美国幽默文学奖得主 ...
也许最明显的裂隙存在于南非两大主要的部落之间,祖鲁和科萨。祖鲁人是公认的战士。他们很骄傲,会拼尽全力去战斗。当殖民者的军队入侵时,祖鲁人拿着长矛与盾牌就冲上了战场,和对面拿着枪支弹药的敌人血拼。上千名祖鲁人死在了战场上,但是他们从未停止过战斗。和祖鲁人截然不同的是,科萨人一直以头脑灵活而自豪。我的母亲是科萨人。纳尔逊•曼德拉也是科萨人。科萨人也与白人进行了漫长的战争,但是在对手武器装备遥遥领先的情况下,科萨人感受到了武力战争的徒劳,于是一些科萨首领采取了一种更机智的手段。“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些白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他们说,“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长处是我们可以用得上的。与其抵抗他们的语言,不如我们来学学英语。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然后迫使他们与我们谈判。”
“虽说你已经有了开业执照,”他们说,“但是你还需要给不同的人种准备不同的厕所。你需要白人厕所,黑人厕所,有色人种厕所,还有印度人厕所。” “那我这个餐厅里就没别的地方了,全是厕所了。” “好吧,如果你不想那样做,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转为正常的餐厅, 只为白人提供服务。” 他关了餐厅。
如果你申请成为白人,他们会往你头发里插一根铅笔,如果铅笔滑落,你就是白人,如果卡在头发里,那你就是有色人种。政府说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职员盯着你的脸打量一会儿,就能快速得出结论你是哪种人。根据你颧骨多高,鼻子多宽,他在随便哪个选项上打上几个勾,就能决定你可以住在哪个片区,可以和谁结婚,能得到怎样的工作,拥有怎样的权利,享受怎样的特权。
种族隔离就是这么做的,它让每个种族相信,是因为其他种族的缘故,自己才不能进俱乐部的门。就好像门口的保镖跟你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因为你的朋友达伦在旁边,而且他的鞋很丑。”于是你看着达伦,说:“去你的,黑人达伦。你拖了我的后腿。”然后达伦反击说:“去你的,斯威。”现在所有人开始怨恨所有人了。但是事实是,你们中任何一个原本也进不了俱乐部。
我找到了我的位置。既然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那么我可以在不同的圈子之间游走。我还是一条变色龙,文化上的变色龙。我知道如何去融入。我可以和爱运动的小孩一起运动,和书呆子一起讨论电脑。我可以跳进人群里,和小镇男孩一起跳舞。我可以和每个人都产生短暂的交集,一起学习、聊天、讲笑话、送餐。
身为局外人,你可以缩进壳里,默默无闻,让别人看不到你,或者你可以走上另一条路。你通过敞开自己的方式,从而保护自己。你不用因为自己是谁而希望被某个小团体接纳,你只要愿意分享自己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对我来说,那部分就是幽默。我了解到,即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群体,但我可以融入所有正在开怀大笑的小团体里面。我会突然出现,分发零食,讲几个笑话。我可以取悦他们,参与他们的一小部分对话,了解一点儿他们的圈子,然后转身离开。我从来不会在哪个圈子里停留过久。我并不受欢迎,但我也不会被排斥。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打交道,与此同时,我又完全是孤单一人。
这就是街区。总有人在买,总有人在卖,倒买倒卖就是要在全程搅混水。没有哪一步是合法的,也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那个帮我们拿到耐克鞋的家伙,他真的有“员工优惠”吗?你不知道。你也不问。对话只会是这样,“嘿,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以及“酷,你要卖多少钱”。这是国际通用密码。
邦哈尼一开始对我说“我们去街区吧”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就是去那边卖卖碟,或者在派对上做做DJ。结果,我们卖碟做DJ,都是为了在街区里做小额贷款和当铺生意积累资本。很快,后者变成了我们的事业中心。
我们努力地干活干活干活,但不管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这门生意还是在赔钱。我们什么都赔掉了。甚至买不起吃的。我永远忘不了有一个月我是怎么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月。我们太穷了,连续几周都在吃一种叫马洛葛的野菠菜,和学名叫莫帕尼虫的毛毛虫炖在一起。莫帕尼虫真的是最便宜的东西,只有穷人中的穷人才会吃。虽然我从小到大家里一直很穷,但是那种穷,和“等等,我在吃虫子”的穷,依然不是一个等级。连索韦托人看到莫帕尼虫都会说:“呃…还是不要了吧。”这些多刺且颜色明亮的毛毛虫,和人手指一般大小,但是和法国蜗牛不一样,人们可以给蜗牛安一个光鲜的名字,让它们成为高级食材,但莫帕尼虫只能是恶心的虫子。咀嚼的时候,它们的黑色脊柱会刺破你的上颚。而且很常见的情况是,当你咬下一只莫帕尼虫时,它们黄绿色的粪便会在你的口腔中溅射出来。
从外人的角度指责这个女人,说“你走不就行了”,实在太容易。我的家庭并不是唯—一个发生过家暴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经常有这样的事。在索韦托的街道上,在电视里,电影里,我看到过无数次家暴。如果这是社会范例,那一个女人能去哪儿?当警察都不肯帮她的时候,当她自己的家人都不肯帮她的时候,她能去哪儿?离开那个打他的男人,找到第二个男人很可能还是会打她,而且比第一个更凶的时候,她能去哪儿呢?当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而周围的社会会给没有丈夫的女人打上贱民的标签时,她能去哪儿呢?当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个荡妇,她能去哪儿呢?她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