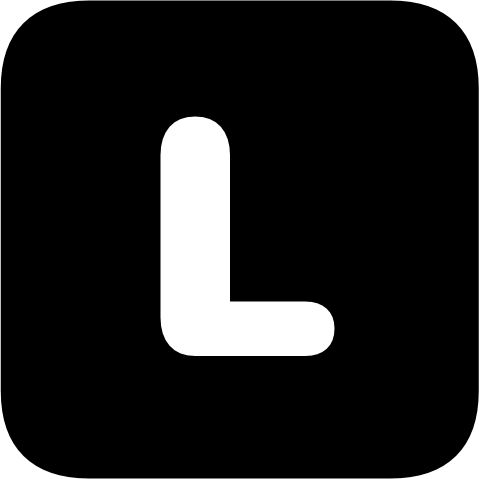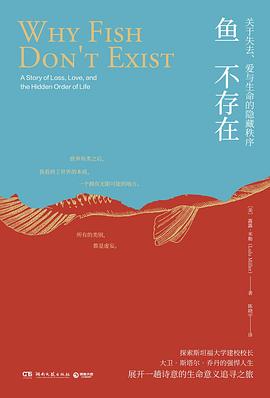露露是本书的作者,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一度感到绝望。所以当她看到大卫·斯塔尔·乔丹的事迹后,不禁产生了好奇: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动力在支撑着他对抗逆境?
大卫·斯塔尔·乔丹是斯坦福大学的建校校长,也是一位分类学家,一个执着于给自然世界带来秩序的人 — 他发现了当时人类已知鱼类的近五分之一。1906 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这场地震让近千个装着鱼标本的易碎玻璃罐坠落在地。霎那间,他毕生的收藏毁于一旦。
在如此巨大的打击面前,大卫没有绝望,他检查了脚下的残骸,找到了他辨认出的第一条鱼,并开始自信地重建他的收藏 — 他用一根缝衣针将标签缝在鱼身上。当世界陷入混乱,他用一根针来重建秩序。
大卫小时候就对花朵很感兴趣,进中学第一天,就把图书馆里「一本关于花的小册子」悄悄带回了家。他躲进自己的房间,坐在桌前,攥着小册子,逐一辨认铺满桌面的花朵,了解他们的种属。哥哥的去世让他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沮丧,也激发了他对植物分类的热情。一个人在经历某种分离、失去或伤痛后,其收藏欲往往会变得格外狂热。
喜欢安静探索自然的大卫,在大学毕业后,没能得到好的工作机会,可能他自己都觉得,这一辈子或许就这样了吧,直到他遇上了阿加西。
阿加西是一位地理学家,他认为传授科学知识的最佳途径是观察自然,坚信自然界中隐藏着上帝所造之物的等级森严的体系。他想组织一场夏令营,让年轻的博物学家们去直接接触和观察大自然,正好一位富有的地主贡献了一座岛,阿加西就在这座岛上建立夏令营基地,并在报纸上招募学生,看到这则广告的大卫自然是喜出望外,以最快的速度申请入营,也顺利收到了录取信。在岛上,大卫被阿加西选中出海捕鱼,那也是大卫第一次接触到海鱼,也正是这些鱼为大卫接下来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向。
离开岛后,大卫将研究重点投向水面。「鱼类文献既不准确,也不完善,该领域看似大有可为」。他带着小伙伴在各水域研究捕到的鱼,并发表相关的分类学研究论文,阐明物种间的新关系。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用各种想到的学到的方式捕鱼,甚至剖开鸟和鲨鱼的肚子,寻找漏网之鱼。收获也很丰富,他们命名了八十种新的鱼,生命之树上的八十个新物种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八个月后,大卫回到了印第安纳州,成了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基础科学教授。还结婚了,新娘就是当时在岛上的一位植物学家。岛上之行给大卫的生命注入了目标,而目标让一个人焕然一新。仔细研究被解剖的鱼类时,大卫认为自己在揭晓真正的创世故事,即生命需要经历怎样的试炼才能成为人类。他们把鱼保存在一罐罐乙醇溶液中,堆在室内的架子上,结果一场火灾毁了所有的标本,而他的回应方式也很简单,再访美国的各个水域,重新收集被毁掉的标本。
他的个人生活也遭受了重大打击,火灾后的两年,妻子感染了一种让医生束手无策的肺炎而死去,最小的孩子也在妻子去世后不久离开了人世。不过大卫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处理完后事后,不到两年,就再婚了。
有数百项科学发现的荣誉在身,大卫被一对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夫妇相中,后者想聘请他担任一所学术机构的首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斯坦福大学。大卫答应了,因为薪水丰厚,学校所在地气候宜人,也有足够的自由度。有了足够的资金,大卫终于可以踏上过去梦寐以求的全球鱼类标本收集之旅。一路上,他们发现的鱼接近一千种。
大卫这种梦幻般的生活,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简·斯坦福。她对大卫在鱼类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感到担心。她希望斯坦福大学能够在其他领域取得进展,比如关于招魂的科学研究,因为斯坦福大学建立的初衷就是纪念斯坦福夫妇的儿子,而简·斯坦福又热衷于灵媒,自然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大卫觉得这一想法不可理喻,两人都互相看不顺眼。
不管怎样,大卫依旧醉心于自己的鱼类分类事业,但随着大卫带回来的鱼类标本越多,宇宙的回击也越猛烈。捕鱼时的伙伴、最喜欢的一名学生都不幸去世,连他最疼爱的女儿也因为感染了猩红热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人们心中感到无助时,强迫性的收藏行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于是大卫又转向水域,回到海上,不断搜寻更多的鱼。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斯坦福和大卫的矛盾越来越深,大卫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出人意料的是,1905年初的一个晚上,简在夏威夷旅行途中意外去世。看来,宇宙总算让大卫喘口气了。
一年之后,一场大地震把大卫的成果撕得粉碎,而他在一片狼藉中,用一根缝衣针重建秩序。而生活中的露露还困在生活的牢笼中走不出来,开始写小说来逃避现实。在绝望之中,她迫切地想知道大卫奋勇向前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绝望的哲学」这本书中,露露貌似找到了答案。大卫坦诚:科学世界观的问题在于,当你用它来探寻生活的意义时,它只会告诉你一件事:徒劳无功。那应该怎么做呢?他的建议是:不要闲着。快乐来自做事、帮助别人,充分应用各项感官,把握当下。此时此地,天这么蓝,草这么绿,阳光如此耀眼,树荫如此怡人,无处能及。继续探索,露露终于在大卫的回忆录中找到了那不可摧毁之物:人类的内心永远比人类能做的事强大。是人的意志决定了命运。
到这里,露露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但好奇心驱使她继续探索,切入点就是 1905 年,简·斯坦福的意外身亡。通过阅读历史记录,拜访对此颇有研究的人,简的死亡疑点越来越多,个个都指向大卫。虽然大卫通过各种手段排除她被毒杀的可能性,但简的症状实在太像被毒杀了,而且从尸体中发现了士的宁晶体(一种剧毒)。在翻阅「鱼类研究指南」这本大卫的著作中,露露发现了一个细节:在「如何捕捉鱼类」这个章节,大卫向读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最喜欢的用来对付最麻烦的鱼的诀窍:下毒?而推荐的毒药就是他称为「世上最苦的东西」:士的宁。
简·斯坦福去世后,大卫被董事会架空。注定闲不下来的他开始被另一个使命所召唤。在过去捕鱼的旅程中,他曾经在一个小村庄里见到过社会边缘人群组成的社区,这些人都有较严重的心理或生理疾病,在这里,不正常才是正常,那些在社会上没法生存的人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得以繁衍生息。一些人在这个村子里看到了美好,而大卫则将其描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陈列室,称这里充斥着「智力不如鹅,仪态不如猪的人」。
如果只是心理上的反感也就罢了,但学者总是爱往深层去想,他担心这个村子证明了阿加西的观点,即动物界会出现一种现象:退化。他担心那里的人正在退化为「新的人种」。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警告公众这种慈善行为的危害,在书中,他建议彻底除掉这些「白痴」,并将其作为阻止全世界范围内人类「衰退」的唯一手段,并开始大力推广「优生学」。
大卫将人的所有个性特质都归因于遗传,贫穷、懒惰、给鸟儿分类的能力,全都流淌在血液中。他开始向政治家游说:只有人类优质繁衍,国家才能长久。那应该怎么做呢?很简单,切除「不合格者」的生殖器官,就可以保证「每个白痴都不会有后代」。为了推广优生绝育,他尽其所能,将它写进了法律,而他自己则担任优生委员会主席。
虽然实际的绝育比例不高,但优生学开始影响更多的人。1916 年,一个名叫麦迪逊·格兰特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优生学的书,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名叫希特勒的德国人奉为圣经。在这本名为「伟大种族之延续」的书中,作者提出了一项政策:政府应该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将整个国家所有「道德败坏、有精神缺陷和遗传缺陷的人」骗到一起,然后对他们实施绝育手术。
直到行将就木时,大卫依然是优生学的狂热信徒,没有任何临终时的醒悟或忏悔。这不禁让作者露露好奇,曾如此投入地照顾「隐秘角落里微不足道的事物」的男孩,怎么会变成一个对曾经保护的东西拔刀相向的人?他在人生的哪个岔路口改变了方向,又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这个选择?
答案似乎就是他引以为豪的那枚厚实的「乐观之盾」:令人发指的自信,相信自己想要的就是对的。当他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有利于进步的正当途径之时,他扫清道路障碍的能力也成倍增长。但露露觉得还缺了点什么,于是她又回到大 卫最初登上的那个岛,那里导师阿加西在年轻的大卫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自然内部建有一架梯子,一架自然阶梯,一个细菌在下、人类在上的神圣等级。这个想法重塑了大卫的世界。过去他那为人不齿的收集花朵的习惯,转变为「最高等的传教工作」,他内心的空洞一下子被这个目标填满。
但是自然界中,每一个人类自认为有优势的领域,动物都更胜一筹,达尔文告诉人们,世上没有阶梯,我们所说的阶梯不过是一种想象,与其称之为真相,不如说它是一种「便利之举」。为什么大卫没能看清这一点?为什么他如此维护这一无端的信念,认定植物和动物应当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或许是因为,这信仰带给他比真相更为重要的东西。
不管大卫何时放弃对阶梯的信仰,都意味着他重新回到混沌之中。他被打回原形,又变成了那个迷茫的小男孩,在夺走了哥哥的世界面前瑟瑟发抖。那种跌进世界缝隙的感觉,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这就是梯子对大卫的意义。一剂解药,一个立足点。露露虽然鄙视他的做法,但在某种层面上,他所追求的正是她渴望的东西。
大卫的故事似乎就这样结束了,他得以全身而退,没有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但这个混沌世界还是偷走了对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基于大卫为鱼类分类事业做出的贡献,分类学家意识到,鱼类这个公认的生物类别,并不存在。鸟类存在,哺乳动物存在,两栖动物存在,但就是鱼类,并不存在。在鳞片的掩盖下,它们是不同的物种,就像那些山上的生物一样。这个对大卫至关重要的分类,他陷入困境之时寻求慰藉的种类,他穷尽一生想要看清的物种,根本不存在。
书的最后,露露的人生也开始回到正轨,重新找到了心爱的人,开始相信,在「实现目标」这个单一的人生轨迹之外,有更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你。